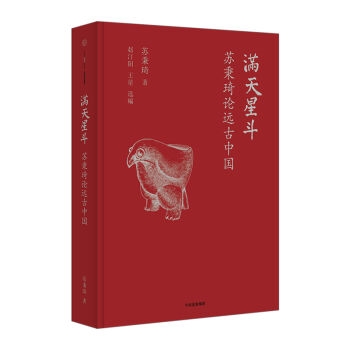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
苏秉琦先生(1909-1997),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专家,与夏鼐先生同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第yi、二届副理事长。曾主持河南、陕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主要遗址的发掘。
【内容简介】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直至夏商时期,都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苏秉琦先生将之形象地概括为“满天星斗”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历史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就中国文明的起源引发了许多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满天星斗》由哲学家赵汀阳为广大读者精心挑选和编排了能代表苏秉琦先生学术思想和风格的文章:关注考古物证所能开发的思想,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展开几近哲学的分析和推想。
【精彩书摘】
苏秉琦自述,他至今六十年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两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两个方面:一是绕出两个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和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二是找到新的起点。其中第二阶段可以1975年开始提出区系类型学说为起点。苏秉琦认为,自己在这二十多年中又走出了两步:一是从宏观角度,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用区系观点选择田野工作重点并做理论探索,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中国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二是从微观角度,应用分子分析方法,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对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找到它们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钥匙。
问: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古兆申先生曾拜访您,就《明报月刊》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向您请教。但他公务缠身,匆匆回港,委托我继续做这件事,我代表《明报月刊》编辑部向您致谢。
苏秉琦(以下简称苏):我正式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已六十三年,算得上是考古界一个老兵,把所知、所得公之于世,是我的职责。
问:第一个问题是,1986年您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文化与文明》讲话中提到,对中华文明的思考,今天已不像“五四”时代那样简单,而是要构想如何建设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文明,引申出来的思考就是:中华文明的民族灵魂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这其实也是当今中国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由于当时您讲话的对象是考古界,着重谈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对后面的问题未做详述。现在希望您具体谈一下这方面的想法。
第二个问题是,在您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中说,中国远古史涉及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公社到国家。中国考古学半个多世纪的发掘与研究,证实这两个阶段的文化一脉相承,否定了20世纪初中国人种、中国文化外来的看法。从旧石器时代到今天,中国文化的发展连续不断,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么,关键性的原因是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抑或是特殊的物质文化造成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
第三个问题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是以什么物质文化条件的出现为标志?西方考古学的论点是以文字、城郭、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为重要标志,但中国考古学界近二十年的讨论冲击了这种认识。牟永抗、吴汝祚两先生在《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化起源若干问题》一文中,以水稻、蚕丝和玉器作为中国原生文明的重要特色。他们认为,对说明中华文明起源来说,宗庙比城墙更重要,而玉器作为一种礼器,也达到了很高的意识形态层次。我们是否一定要用文字、城郭来标志文明呢?中华文化作为一个连续发展的文化体系,可否归纳出标志自己文明起源的特质呢?
第四个问题是,“玉器时代”的提法能否成立?“玉器时代”相对于“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代而言,似乎更能体现中国文明的特色。这一提法,和其他三种时代的提法,出发点有无不同?学术界有无争议?
第五个问题是,您以“区、系、类型论”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六大区系文明,上古的神州是多民族、多源文化并进发展的格局。秦统一后,中国仍是多民族国家,但是秦始皇提倡书同文、车同轨,又统一度量衡,使中国文化走向一体化。那么,此后先秦时的多源文化是否仍涵涉其中?秦汉的统一对中国文化往后的发展会不会改变从前那种多姿多彩的面貌?一体与多元有没有矛盾?统一的作用是积极性多,还是消极性多?
第六个问题是,您提出的“区、系、类型论”已成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理论。但用这一学说来论述秦以后的中国文化发展,是否依然适合?就我所知,即使对论述新石器时代也仍有争议,如安志敏先生在《论环渤海的史前文化——兼评“区系”观点》一文中所述。您对此有何评议?
苏:古先生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说明他对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很了解。他所提的六个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大题,即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史学、考古等学科研究中的作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即中国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的特点与道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即精神支柱、民族魂)是什么?对于这三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是我一生奋斗的中心。1994年,当我八十五岁生日时,我的学生写了几十个字祝寿说:“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间而启示当今时代的,将永为师表。”他们就是这样理解我的。
在具体说明这些问题前,先叙叙家常,算作背景材料吧。我的学生和朋友编辑、出版了我的第二本论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我写了一篇不足两千字的自序,题目是《六十年圆一梦》。我的梦就是考古学的科学化和大众化。这个愿望现在已实现了很多,《明报月刊》的来访及所介绍的读者的关心,也说明了这一点。科学化、大众化是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必然归宿。我六十年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两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两个方面:一是绕出两个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和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二是找到新的起点,即从对一种古器物(瓦鬲)的研究到对一种古文化(仰韶文化)的研究。这个新起点,对以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是具有相当意义的。
第二阶段可以从1975年开始提出区系类型学说为起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我不停思考这个学说的十年);1980年时我又说“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此时这个思想已经成熟。“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二十多年,是中国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好时期,区系类型理论得到普遍应用、检验,日益完善,成为我国大多数考古学者的共识,发挥着基础理论的作用。我在这二十多年中又走出了新的两步:一是从宏观角度,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用区系观点选择田野工作重点并做理论探索,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中国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二是从微观角度,应用分子分析的方法,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对中国文化传统中起长期积极作用的因素,找到它们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钥匙。这是在前一阶段工作基础上合乎逻辑的发展。我和许多朋友已经走过了第一步,正在用心地走第二步,《明报月刊》读者关心的三大问题,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得到现有认识的。